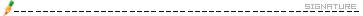真是糟糕透顶。不敢看了,实在是不敢看了。这个叫张岚的家伙自己都被快自己心里深深的郁闷给折磨疯了。烟已经抽完了,他的心情一点也没有好转,好象又更进一步了,他的眼眶里明显有什么晶亮的东西在打转转。我很不屑地瞥了他一眼: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一个大男人遇到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用的着儿哭吗?可我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不大对劲的地方,我低下头一惊,赶紧抹了把脸。天啊,真是的!我自个的泪水什么时候已经掉下来了?都连成线了。算了,我不想再看这个倒霉蛋了,天知道这家伙遇到了多么令他不快活的事情。看他的样子,他是不会告诉我什么的了。
正当我想挪开视线的时候,张岚似乎是预先知道了一样,他好象是不想放过我了,一定要让我死死地盯着他才行。所以,他做了一个令我惊恐万分的动作,使我再不敢把眼光移开半步。我紧张地冲他吼了起来: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这家伙不知道从哪个我没注意到的拐子里拿了把十分锋利的菜刀出来,紧紧地握在左手上,高高地举着。他不回答我,而是万分憎恶地瞪着自己的右手。张岚!我还没有喊出声音,他就把高举着的菜刀朝着右手狠狠地落了下去。虽然还未来得及见到血,但我已经被吓得昏了过去。
在张岚抽着烟郁闷的同时。不过,当然是他那一刀落下去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因为他落下去的时候我就昏过去了。既然是昏过去了,我就没法儿给你说这些事儿了。咱们回到“同时”。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做这一件事的时候,在我们所没有看见的地方还有其他人同时做着和我们一样或者不一样的事情。没有理由我们停下手上的活儿去看他们,他们也没这个可能。这可是绝对的。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在张岚郁闷的同时,在另一个房间里一个叫王峰的男人正做着和张岚的处境截然相反的事,是一件对于男人来说快活无比的事情。至于是怎么做的,我就不去细说了,想必那点事情大家早就心知肚明了。
这两个房间说离的近也不是很近,既不是隔壁也不是对门。但也算不上多么遥远,至少是在同一个城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我一些问题,譬如为什么要在这儿说到王峰呢?如果我不回答你,我知道你一定会说他们之间有着某种
他们两个,一定要说有什么关系的话,就像咱们走在大街上,同我们擦臂而过的千百万个陌生人同我们的关系一样。两条压根都不相交的平行线能扯上挡儿么?不过这并不防碍我来叙述王峰这个人。因为我看到了王峰身上与史以来就有的后来张岚也有了的特别的地方。而且,虽然张岚跟王峰这辈子从没有接触更不用说认识过,不过后来张岚确实是知道了王峰这个名字的,也总算是搭上点边儿。但这是后话,咱们放到后面去说。
这个时候,天确实阴沉得很,我想很有可能也是张岚感染的。天空黑压压,灰蒙蒙,看来是非要下场痛快淋漓的雨才舒坦。不过在雨下来之前,王峰和她的女人已经开始翻云覆雨了,他们床上的反应比天上的骤变要强烈得多了去了。等到天空开始滴落雨点的时候,他们已经接近尾声。再到窗外倾盆而落的时候,他们正紧紧地贴在一起疲惫地喘着粗气。比起倒霉蛋张岚,他们可真是幸福多了。此时,王峰的女人正背对着他,他从后面紧紧地抱着,双手从后面温柔的放在女人丰满的双乳上。女人很累,满足地闭上眼睛想要慢慢睡去。王峰依然在深深地沉醉着,他还在用双手去一点点抚慰和欣赏女人的裸体。他的手指在女人顺滑的肌肤上一寸一寸缓慢地嗫嚅着,移动着。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细节。王峰在抚摩女人的同时,他的右手手指还有一个很细微的不自然的动作。小拇指在女人的身体上摩挲着,但是中指却在一遍一遍磨蹭着紧挨着的无名指。那个无名指并不完全,只剩半截。愈合的断口圆圆地突起,表面不平,有点像被弃置已久的已经剁好的肉馅儿,模样狰狞。王峰摸着摸着,表情逐渐扭曲起来,起先舒适的快感一扫而去,似乎那愈合的断口又被撕开,流出血来,很疼。女人已经睡去了。王峰穿了裤子起来将窗帘拉开一个小角,然后坐回到床上点了根烟。这时,他也成了一幅和张岚一个模样的苦瓜脸。看来,这根残断的指头摸在女人的肉体上,令他感到十分的,千分的,甚至万分的不舒适。这无法形容的不适令他感觉颓唐以至恼怒。
雨后天晴。日子还是像往常一样过。张岚在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之后又回到了单位上,大家伙儿的中间。他的单位是晚报报社广告副刊的编辑部。他就是这里发布广告的编辑的一员。和这个城市的很多人比起来,甚至跟这个编辑部的很多人比起来,他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但是这一天,大家格外地注目这个平日没有注意到的男人。他的头发,他的脸,他的衣服,他的整个人都还没有摆脱一个星期就有的苦瓜味道。知道内情的人都在暗地里深深为之叹息:唉,可怜的男人!男人的心情是跟着两样事情转的:
可惜的是现在张岚两样都落了空,女人走了,奖金飞了。所以他郁闷无比。不过他本来就是一个没什么趣味的人。那么今天大家为什么要注意他呢?他又没什么改变。问题不这儿,问题出在张岚的右手无名指上。大家盯直了那根指头看,好奇而惊异。这根指头现在很肥,少了半截,裹着厚厚的白纱布。有人问他怎么着儿了,他头也不回,径直朝着自己的位置上,话也直冲冲地从嘴巴里蹦了出来,似乎那话并不是从张岚的嘴巴里出来的,而是从**管子里被射出来的。其实就两字:剁了!
听得人心惊胆战。问的人一脸狐疑,看着张岚悲壮的表情一时半回儿说不出话来。心里却默默念叨着:这家伙,我看他是去精神病院休假去了!张岚不管那么多。是的,他很悲壮,一副气势磅礴,视死如归的样子。他也很痛快,简直是痛快极了。他脸上的郁闷顿时因为这两个字消失的无影无踪。他坐在位置上,意气风发,阳光灿烂。看来,真的是雨后天晴了。是啊,剁了。这意味什么呢?无名指没了。无名指又意味着什么?那是戴结婚戒子的地方,是爱情证明的归属。戒子取了,扔了,可以再戴上,再买回来。
可是这指头没了,那就是准备以后再也不戴了。张岚笑嘻嘻的,十分爽快地对着旁边的哥们说:钱嘛,没了可以拼命再赚,女人,去你妈的!咱以后不想这挡子事儿了!然后举起了他那肥硕的半截无名指使劲在同事面前晃了晃,像摇曳着一杆胜利的旗帜。瞧见了吧?这就叫有种!以此看来,张岚真是个有种的。“这挡子事儿”指的既是过去的历史又指未来可能发生的同样的事又指跟女人之间这件事的本身,含义丰富极了。所以,他那当着我的面剁掉的半截手指的重量就可想而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