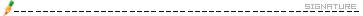1967年元旦我是在武汉过的,可以说是载誉而归的在汉停留没几天,我就回枣阳了。回枣阳,我第一印象和感觉就是枣阳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小了。
这年的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各级党和政府领导权的狂暴行动,“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国夺权”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比前一阶段,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
回枣阳后,学校派系斗争已炽热化了。
两派阵线分明,以“钢高二二”为首的张×与县“东方红”的孙政治观点一致斗争目标相同。我们班的保守派(即保皇派)为多称之为“大联合”,造反派只有五、六个人,他们依赖“钢高二二”,多次把团支书朱帮国、还有李其明拉出去斗(在吴店教堂),有时候就在我们的教室里斗,将课桌垒起来,“架飞机”。“文攻武卫”是江青的杰作。幸运的是我只亮了下相(即站在垒起的课桌上),但他们没有对我动武,斗我的理由好像是我亲近了黑帮老师。
我尊师敬长是潜意识的,爱他人胜过自己,是与生俱来的品质。包括我后来当上了生、杀、予、夺在握,人、财、物、案独掌的检察长时,我对被审查对象也一样施仁政,文明执法,善待犯罪嫌疑人。这是我的禀性使然,一生没有私敌。1994年8月盛夏酷暑,我让办公室张德平主任将我用的电扇(那时没空调)送给羁押室,那里面关有好几个犯罪嫌疑人。在我当检察长期间,无数次地参加了刑场监督,我对那些执行任务的法警、武警战士,反复提醒不要对极刑犯实施拳打脚踢,而且要求他们一定要瞄准,不能偏离,最好不要增补第二**,尽可能减轻刑犯的痛苦,做到斩立决。对尸体,我要求执刑人员也不能诬辱,保全尸首完整(医学解剖除外)。
春节过后,全国性的红卫兵涌动没有消停,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提倡徒步大串联。我与一帮同学结伴,由枣阳火车站徒步走到唐县镇,就不想走了。夜色来临,扒了一列货车,当晚就到了武汉。停了两三天,又由武昌扒乘货车到了长沙,驻在一家砖厂,稍稍休息了两天,就真心实意地徒步从长沙到韶山冲。长沙到韶山的土路被我们这些红卫兵踏得像水泥路一样,黑亮黑亮的。长沙的大米饭口感极好,既像东北的大米,也像我们襄樊的糯米,晶莹剔透,香气袭人。
到了韶山毛主席的故居,我也是走马观花。在他的卧室,我乘讲解员讲解时,坐了一下老人家的床,还是被发现了,讲解员狠狠地训斥了我,我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我们每人发了一枚韶山纪念章,还看了故居左侧的晒谷场。按照土改时成份划分的政策,毛泽东家定为富农成份,应该说是合适的。
人满为患,疏导及时。
没在韶山过夜,我们就返回长沙了。接着同学们建议到江西井岗山革命根据地。那时真的有目的又无目的,信马由缰啊。搞不清从哪里去井岗山,只好奔南昌。南昌有一个八一广场,酷似天安门广场。我参加了一个批斗会,被斗的是名女干部,我印象最深的两点:一是她姓万,二是头发剃一半(阴阳头)。我还是那句话,对被斗的人,我恨不起来,我一生中不树敌,也不轻易恨人。
但一生中,委屈我的也有两个人,一是结束我军旅行生涯的人,再就是结束我政治生命的人。我是他们政治斗争中非常无辜的牺牲品、替罪羊,况且我对他们尊重、服从有加。事后,这两人评价我只有两个字“好人”。好在上天有眼,他们的结局不是一般的糟糕,这叫报应;我的政治生涯善终,比预料的更好,这叫因果。
在南昌停留的时间不长,返程经九江、武汉又回到了枣阳。
在回到家乡九连墩下月池堰,遇到了田明书幺姑,她告诉说我的妹妹夭折了。这对我的打击很重。听母亲说,妹妹得的是急性脑膜炎。如果这位妹妹不走该多好啊。在妹妹夭折的两个月后,我慈爱的祖母也去世了,那是我相依为命的亲人,我永远怀念她们。
在家呆得很无聊,只好又返校。那时两派势力,随着武汉 “7.20”事件的发生,派性斗争升级为武斗,打、砸、抢成风,大揪党内、军内、公检法机关内 一小撮儿,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和群众再次惨遭迫害。造反派以“武装左派”为名,抢走县人民武装部**支**。紧接着的9月13日,造反派所谓的炮轰公、检、法联合作战兵团进占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虽然驻枣联络员武笔峰的文章为我们大联合撑了腰,但地方形势始终还是受北京影响。孙×还坐上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交椅,我们学校的那个张什么也捞了个委员,于是本已成优势的大联合转为被动了。我校组织了枣二中大联合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转战在枣南琚湾、熊集、耿集一带。这支宣传队有20余人,以女同学为多,朱帮国是队长,申温国主琴,实际就是一把二胡,我是他们的助手,其它锣鼓家什各有其人。在走村串户期间,演出是次要的,串联发表观点是主要的。为防造反派的追杀,我们白天扮作农民,晚上演出、串联。
两派斗争虽然激烈,但有些目标却是一致的,如破四旧、立四新、抄家、批走资派、贴大字报、游行示威、批封资修等等。但比较而言我们“大联合”温和些,而“东方红”激进些。
大概转了个把月,我们各自回家了。随着国家文革形势不断地变幻,心、身均无所适从,唯一期盼的是最新最高指示,这是中心的中心。
在回到家乡赵湖大队的日子里,我成了各派拉拢的中心人物,都在做我的工作。
大队各派组织搞革命大批判是很搞笑的,找五、六个人围着大队书记唐家美指指点点的。唐家美,是年轻有为老资格的书记。大人训斥孩子,就说:“再狂(闹),唐书记来了。”一下子,孩子就乖了。虽然我现在官至正七品,但见到他这个已是耄耋之年的大队书记,心里还有些发怵。
这年底搞清理阶级队伍,我在一队槽门湾。住在李群恭阿姨(现任襄樊市卫生局党组副书记田明亮的母亲)家。上面来的有工作组,组长是我初中时的同学,姓余(当时在枣阳火车站供销社工作),俨然像个钦差大臣,贫下中农对他诚惶诚恐。而我不以为然。我是周边几十里中少之又少的高中生,而我的背景也是当地较为显赫的,我父亲是正儿八经从部队转业的19级国家干部,当时的副县长也很少能达到这个级别。大队还组织了赵德金、陈永龙、郭永发以及我为骨干的工作专班。
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大队的走资派,当然是那个唐书记。我感到指挥或左右这个运动的,还是这个靠边的唐书记。倒霉的是地富子女,可怜兮兮地被斗来斗去,毫无结果。
本年,中国人民解放军8229部队驻本县,执行“三支”(支工、支农、友左)“两军”(军管、军训)任务,混乱局势得以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