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中一日(发表在06年佛山文艺)
森林里那一排白色的围墙隐隐约约在半山中露出一个边。他从山下的大型停车场向上看,山林里升腾着一股绿色的雾气,漂浮在晃眼的白色阳光下面,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头小径隐没在依山岭向上延伸的密林里,不时就有一截露出来,一个盘旋又不见,象猛然拉上一面绿树绣的屏风,石头小径是白色的,吸着阳光,点点的白光,就是在树林完全掩映下也能感觉下面的如流动的连续。他送走了妻子,看看时间,也到了吃饭时间,就进了前面小街的一家餐厅吃晚饭,因为人少的原因,一个女服务员不停的和他搭话。她二十岁左右,脸盘瘦削,皮肤苍白,有本地人特有的高颧骨和浓眉毛。餐厅里连他现在就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个背了巨大的登山行囊,神情疲惫,头发凌乱,鞋上衣服上都沾满了草汁和泥巴的少年,估计是才爬山下来,饿的只狼吞虎咽地对付饭食,恨不得把筷子吞咽下去,那意思无意和任何人交谈。女服务员就只好和他搭话,他不动筷子,要了瓶红葡萄酒,坐在四方形几乎落地如门的大窗边上,端着杯子一小口一小口的抿,这付样子到是一个很不错的聊天对象。
“你的妻子怎么没有来?”她问。他和妻子这几天是这的常客,这个餐厅虽然小,但是干净雅致,十几张小桌子,窗外有回廊,草坪和竹林,还有剪的整整齐齐的象小土包一样的桉树,隔了窗就看见一派绿竹,掩映着远处一块巨大凹地的明瓦闪光,那儿是一家宾馆的房顶。“她有事情回去,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他苦笑一下说。“你没陪她回去?哦,你还在这呆多久?”“她处理好事情就来,我就在这等她,至少还会呆上一段时间,这不错,我想起码要在这度过夏季。”他又倒了酒,这一会他挺想说话。“我们这的夏天到是凉爽。”她很自豪的说。“的确如此。”他点点头。“喜欢这儿?”她问。“当然喜欢。”他又点点头。“我到是总琢磨着去大城市看看。”她想了一下,提供相反的论调:“每一种生活都有不足之处,人总想动来动去,甜的吃多了就想咸,咸的吃多了就想甜。”“有这方面的打算?”他一口喝干了杯子里的酒。“打算?噢不,还没有上升到打算的这个范围中,充其量不过是偶尔对平淡的抱怨,对我来说,真做这样的打算是需要勇气的。”她羞涩地一笑:“需要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诱发这样勇气的机会,或者一个变故,能叫我把抱怨变成真实行为的变故。”他笑了,“那到是。”“不过很难。”她坐到窗户下,颇有点忧伤。“太平淡了,连变故都可望不可及。”他想了一下,提醒说:“我看所有抱怨积累多了,我想也就自然的形成变故,不一定是要外力形成。”她琢磨了好一会说,“但是有时候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那种抱怨,多数情况是不确定。你要知道,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很少有确实明白自己想干什么的时候。”他闭目想了下,“确实,大多数人都这样。”
吃完饭他彬彬有礼地告别了饶舌的小姑娘,她说帮他把只喝了半瓶的酒保存起来,明天还可以喝,以免浪费。他笑着同意了,带着半瓶葡萄酒作用在血液里的微醉走到小街上。小街不过几十米,除了餐厅就是卖纪念品的商店,稀稀疏疏的就只有几个人在走动,一条黄毛大狗神经质的从街头跑到街尾。又从街尾跑到街头,如此反复,似乎在享受着晒热的街心石子对脚掌的按摩。
小街的尽头就是通向半山那个宾馆的石阶,并且可以一直通到山顶。他走到石阶处,从茂盛的树林中吹出来一股风,刚才还安安静静的空间被此起彼伏的声音充满,哗啦哗啦的响,天空被远处的山脊藏起来一半,只剩下小半个藏青的天空。他走了一阵,一回头,发现沉寂的平原已经可以尽收眼底,白茫茫的阳光象是雾,那些树林和房屋微小的象玩具,田地象棋盘,间或有白亮亮的池塘夹杂中间,象破碎的白玻璃。山脉两边向前曼延出渐渐变小的丘陵,一直插入辽阔的平原中,一条马路清晰可见,在其中盘旋而去。他想妻子现在应该已经到家了,她开车一向很快,二百公里三个小时就应该到了。他坐到石阶上,突然有点后悔,他本有足够的时间对刹车线动手脚。想到这上面,他一哆嗦,侧面吹过一阵风,头顶上伸过一枝大榕树全部的荫凉,浑身都抖索着大片大片榕叶的阴影。他后退了,他下不了手。不,他不是放弃了。他对自己说。他眯着眼睛看石阶旁边伸出老长的野蔷薇的枝条,头顶上一点殷红,在微风中颤动,象一粒正在下滴的血珠。他忙跳过目光,不敢在看,目光一杨,却见山风越过斜坡,如波浪一样在树林上渐渐远去,好象自己也被那风拉着在跑,身不由己。他想起那天突然产生的念头,心头一寒,眼睛里就过滤掉漫山遍野的绿色,就象心里的念头喀嚓一响,拍出来一张黑白照片,吐到眼前,有山影,树影,草影,可没了颜色雕出来的立体层次,只剩下黑白的一个平面,冷冰冰的。
他回到山腰宾馆的房间,只躺了一会就接到妻子的电话,她说可能要过两天才赶的回。他说:“别忙,事情办好了在来陪我。”她没接话,匆忙地说了两句就挂了电话。他温和地对自己笑了笑,见窗口的印花厚窗帘突被风吹起,隐隐传来雷声,从窗户看不见天空,贴的很近的山壁象巨大的碉楼隔绝了他的视线,在阳光一扫而空的阴沉里,一排排植物拉出潮湿的身影,象一队队排列整齐前进的古代士兵。他心里郁忧,把窗户关上。几粒大雨点打在窗玻璃上,啪啪的炸开,一头撞在玻璃上的狂风把水痕吹成片片疤迹。他拿了香烟,把窗帘完全拉开,能看见侧面一个凸出的白色大阳台,雨雾弥漫过来,一片淋漓细雨淡淡飘出,雾气一样从修理的平齐的草坪上滑过,中间夹杂着大粒大粒却稀少的大雨点,打在草坪上啪啪的响。他盯着那个阳台出神,拼命的把思路拉开,他有些承受不了。那个阳台这一会沥沥都是水,雨水敲打在栏杆,那是旁边的房间,好象是有房客的,可几天从没见过,静悄俏的也没一点声音。天空中出现一个闪电,接着一个闷雷象个气喘嘘嘘的老人一样爬过来。他在阳台上好象看见了一个人影,他把思路尽力拉到这上面,那是个什么人呢?他想。可是只想一会又一不小心拐回来,他要杀了她,他想。瓢泼大雨拥挤在山壁到宾馆的中间空地上,发着奇异光芒的雨丝充满着仅有的空间,草坪上积了水,肥甸甸的肿胀起来。他想他已经决定了。他看着从紧紧簇拥的林木间流出几股白亮亮的水,越过铁枝,逼近围墙,却被围墙前的引水沟轻松引走,他的思路开始懒洋洋起来,坐在这个深山寂廖的房间听着僚杂的雨声,以及雨声里一切音响动静,有潮湿的鸟啼,不知藏在何处,不时就透过愈加安静的雨声扩散过来,有树叶和草丛的响动,扑扑嗉嗉的,天慢慢就黑了下来。
他给妻子打了电话,手机一通,他就隐隐听到有音乐声,瓮声瓮气的音乐,只有处在极大的厅堂里才会有这样的回声,他漫不经心地问她现在在那里?她告诉他在吃饭,陪一个朋友。他没继续问,陪谁吃饭他知道,她下午匆忙地说一个人要回去一趟他就不动声色的打了个电话,给他一个朋友,和那个人在省城同一个部门。他轻易的就搞到了他需要的情报——那个人在派往他这个城市的一个考察团里,正是今天到。证实后他竟然笑了,舒透的笑,妻子在洗澡,他在阳台上,挂了电话他回到房间,侧耳听了听卫生间里哗啦啦的水声,心里舒服,竟然没有一点嫉妒和愤怒,一点也没有,挂在墙壁上的钟当当地敲了四下,房间里阳光充沛,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折射着从窗户斜射进来的阳光,五颜六色的分布在暗色的地毯上,斑斑驳驳,涂着浓浓黄彩的床头,两个凌乱的白枕头可笑的压在一起,昨天他们还在同床而眠,相拥共枕,他身上缠绕着她全身的感觉和气味,头发的柔软,皮肤的热量,肉体的弹性,这些感觉现在象一明一灭的灯火,亮的时候心里满是兴奋,暗的时候只有憎恨。他想着晚上听着她鼻息的隐扬,在黑暗里他伸过头去看她的脸,她的脸藏在一片暗影里,眼睛轻闭,睫毛柔软地闭合于一处,她的鼻息扑到他脸上,热热的,他是爱她的。他回忆起他们第一个吻,回忆起许多的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分成无数个亮点在他幽静的记忆之河里点点闪烁,他是爱她的。他靠在枕头上,凝视着她的脸,只有在她熟睡中他才能平静下来,她的脸放弃了所有白天的表情,一心一意的属于他,带着孩子一样的安详和自信,也给了他安详和自信。而只有这时候他才知道他是爱她的,她这一具蛰伏的身体才是纯粹的,干净的,平静的。他的心堵的难受,躺在她身边。被她一下一下的鼻息折磨着,他要夺去她的生命?夺去这缓缓而来缓缓而来的鼻息和气味?夺去那些在记忆里和萤火虫一样的光亮?他所有白天的想法就都崩溃了。可现在,他来回的渡步,想一会昨天又想一会刚才的电话,心里奇怪的有一种快感,好象得到了答案。她一会就开车回去,去找那个人,现在还在仔细的洗去身上属于自己的味道,好干干净净地去找另外一个男人。哗啦啦的水声流在他耳朵里,就象一首舒缓的音乐,洗去了他翻来覆去的罪恶感。他坐在椅子上抽烟,一口口地吐着烟气,满房间都是她洗澡的声音,他也象浸泡在热水里,烫的他懒洋洋的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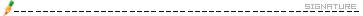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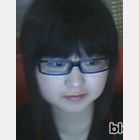

 可以啊,杂不好了尼
可以啊,杂不好了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