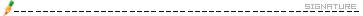漫议郭伏才的诗
老 冒
我已经30年不写诗了,不读诗也有20年了。因为我研究了30多年的文学,竟越来越不知诗为何物。可偶然间刚打开《风笛的吹奏者》,一种久违了的只保存在我的记忆深处的清香扑面而来。这种香不浓不艳,似莱莉花香依偎着我轻轻地弥散开去,似有却无,无中却有。这就是初读郭伏才的诗带给我的淡淡感受。大概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诗味”吧。
从本质上说,人人都是诗人。人有七情六欲,就要抒发要宣泄,就要嘻笑怒骂,哪怕最枯燥的环境,都能激发人们诗一般的激情;哪怕是离诗再远的职业,也不乏诗的灵感和冲动。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可是最终又不是每个人都做了诗人,原因在于仅有情是不够的。诗情之所以为诗情,它另有自己的规定。
并非什么都可入诗的。如果说小说戏剧还具有审丑(本质上也是审美)功能的话,那么诗歌才真正是美的事业。我越来越不喜欢先锋派诗歌,其因素之一就在于先锋派诗歌的创作颠覆了诗的美的殿堂,亵渎了诗的圣洁的境界,狗屎,鼻涕,裹尸布统统入了诗,犹如一桶大粪泼进了祭堂。欣喜的是郭伏才的诗把我们引入进一座美丽的画廊,为我们点染生活的绚烂,为我们摹写生活本来的靓丽。枫叶玫瑰,小溪森林,茅庐古城,无不蕴含别致的诗意;夏日秋天,凤笛古琴,清水烈酒,无不点燃澎湃的诗情:迷失绝望,圣洁征服,握别爱情,无不通往幽邃的诗境。我相信这个世界带给郭伏才的与带给我们的一样,并非全是桃红柳绿
鸟语花香,诗人也有许多的苦涩需要述说,但郭伏才懂得诗的价值在于美,因而这种理解赋予了诗人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也许在有些人看来,郭伏才的诗的对象过于传统,甚或过于陈旧,我却不以为然。能够在传统的诗的对象中发现新的美,不仅独具慧眼难能可贵,重要的是对于诗的美的价值及诗的规律的敬畏。我一直认为,人们之所以还需要一种叫做诗的东西,就在于诗向人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这个对象本身便具有美的品格,而郭伏才做到了。
然而,仅仅提供一种诗的对象仍然不是诗。我们常说唐人把诗写完了,不仅是极言其艺术上达到的高峰后人难以企及,更是说,唐人所创造的诗境已经无所不包,几乎没有什么空间可供后人去填补去超越。当然这是庸人之见。诗的美不仅需要发现,更需要去创造去开拓。从这个角度来说,唐诗给后人留下的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恰是今诗创新的平台。郭伏才就是依凭这个平台继续攀越的人。他的《风笛的吹奏者》奏出的那淡淡的苍凉和颤粟的悲怆,吹出的民族血液与黄河一样的流淌,试问在唐诗中曾有哪一支羌笛为我们吹出过这历史的厚重,又有哪一管竹萧可曾为我们演绎出背负着强烈使命感的心的跳荡。当然诗歌发展到今天,理应拓展诗的题材领域,扩大诗的表现对象,新的生活也使得诗具有了这种可能性,然而没有新的艺术创造,没有新的诗情点化激活这个对象,即便把这支风笛交给丁李白,交给了王维,他们也吹不出这些时代的音符。
诗歌的重要特征在于语言美。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创新。现代诗歌理论在归纳这一特征时将其称为“陌生化”效果。的确如此。杜甫“宁安一个字,拈断数根须”,正是他追求诗歌语言新奇隽永的生动写照。但是“陌生化”不等于晦涩艰深,更不等于生僻险怪,脱离了诗的意蕴追求外在的“陌生化”效果,必是适得其反,过不了三五天恐怕连诗人自己也不知所云了。郭伏才也追求诗的语言的创新,但他的语言创新是与他对生活细腻的体验和内心感受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他所创造的诗的意境不可分割的。如“五月龙舟雨/轻轻斜斜地/从天边洒落/揉成颗颗珠扯成根根线/缀成一挂帘子/雨落在树上落在苹尖上/落在玉兰花上/从风的翅膀上跳下/从房顶上滑过/在清水塘中窃窃私语/”。新奇的感受,新奇的想象,新奇的修辞,新奇的语境,凭添了诗歌无尽的韵味。再如“金
色的稻浪滚动在农夫心底……宛如拥抱自己久别的亲人/来拥抱农夫一年的期望/然后搂疼自己的妻儿/点燃那只久别的烟锅/叭嗒叭咯地/让烟雾缭绕自己/让老酒烧痛自己的心/躺在影于上/静静地睡去”。一幅多么美丽的丰收图画!当我们叹服这幅农家乐时,恐怕已经完全忘却了诗人的语言创造,这也正是诗歌语言美的最高境界了。
在感情上我排斥西方现代派的诗,更讨厌当代一些诗人生吞活噎无来由的模仿,但客观说来,现代派诗歌在其象征手法、直觉表现和幻化变形等方面确有可资学习之处。郭伏才的诗也应借鉴这些艺术技巧以丰富自己的诗歌表现,那样的话,诗人就会插上双翅在诗歌的净空中翱翔。
(襄樊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