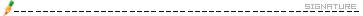抒生活之真情 写诗歌之灵性
——读郭伏才先生《风笛吹奏者》之点滴
谢 冰 凛
我是通过伏才先生的诗歌而走进他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隐者,他在诗歌这片土地上默默地耕耘着,且乐此不疲。这让我顿生敬意。
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离诗歌越来越远,而一个要用诗歌来成就自己,并时时吹响生活风笛、时代风笛的歌者,他给时下空前寂寞的诗坛带来了惊喜。当今世界,当许多人沉醉于在滚滚物欲中歌舞升平,当生活的暴风骤雨总想淹没人类的精神家园之时,还有什么东西比诗歌与音乐更能安抚修补人类千疮百孔的心灵呢?在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纯净的精神世界总是被现实扭曲污染,高尚的情感世界也会携带着世俗的病毒,让人们总感到灵魂的芜鞠和人性的杂草丛生。阳光、花朵、清风、明月……大自然的森林如果没有小鸟的歌喉、人类的寻找便失去了灿烂和明媚。
读伏才先生的诗,心中始终有一股汩汩清泉,时刻洗濯着心中的每一个角落,晶莹剔透与清新淳朴,犹如一方原始的天然氧吧,滋润着心腑。让人远离世俗喧嚣之后尽情地深呼吸和坦然释放,使你的灵魂得到一个空前的静谧、怡然与安静。
诗是什么?什么是诗?或许人们永远会争论不休且无法界定与确认,但作为一个富有灵性且生活在基层的诗人,伏才的诗歌是这样诠释的。他认为诗歌是灵感闪出的火花,是用文字排列成的音乐,是生命合着生活唱出的梵音,是歌者用灵魂吹响的风笛。同时,诗又是心之灵性和独特的审美意向在瞬间的猝然相撞,是一种奇妙圣洁的意念或空灵静谧的精神状态。凡夫先生在序中曾这样评价伏才:说他“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是一个真诚透明的人。”这话概括的十分到位。为诗为人,伏才确实如此。纵观他的作品,我体会最深的有三点:一是用真情抒写诗的灵性;二是用哲理含着百味人生;三是质朴诠释自然与生命。
一、用真情抒写诗的灵性
伏才先生的作品,通通都渗透着一种“真”的情愫,他总是把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照到真善美之上,把诗的灵性抒发得清新又自然。作为生活在物质世界的人,伏才的诗没有沉重,没有郁闷、晦涩,也没有故弄玄虚故作深沉,更没有沾染上一些前沿先锋的意念或惊世骇俗的离径判送。他的诗在真诚浅易中明快生动,那种质朴淳厚、拂去铅华的抒情,更像我的脚下的黄土地和芳草萎萎的绿荫地。他有时就像一个天真无邪、情窦初开的孩子,对生命的世俗与崇高,满怀着新鲜、激动与感恩。他对未来的追求与向往执着而专一,他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心存无限的眷恋之情,他那种单纯率直,自说自话的心灵独白,会不经意地将人带入到一种至纯至美的境界,让读者产生如沐春风的感觉。在他的诗中,始终跳跃着一种灵性,那种生命的真纯与肥美、鲜活与灵动,那种灵魂的细腻、激越与澎湃,还有在特定环境下主体与客体的互相告知与交融,总让人能感到真情与灵性,感到人生的无限甜美和春山午后的禅宗意趣。
如《秋天的歌唱》、《爱的过程》等作品。
二、用哲理含盖百味人生
空灵哲理、日光月光似的情感倾诉,是伏才先生诗歌的又一大亮点。哲学是深奥博大的,而哲理却是浓缩而折叠的。伏才的诗烙着真善美,他的诗之所以有诱人的气息与醉人的芬芳,是得益于真理的含盖与光芒的渗透。他的诗歌,在朴实的语言外壳之下,有一种沉着与内敛,它在一种平铺直叙之间,让我们总看见生命与人性中那饮不完的清洌与甘甜,也能看到青春与激情那褪不尽的颜色与燃不尽的火焰。如《风笛吹奏者》这类诗歌显得即沧桑又大气,它展示的是农业而含着的却是一种生命的根系以及人性的厚实、坚韧与博大,特别有撼动力也具有强烈的净化与提升功能。读这样的诗,那本是沧桑浊流的心,忽然间变得清新朗润起来,而且多了许多不可言传的情愫与顿悟。桑塔耶纳在论及诗及诗人时曾这样说过:“诗人从幻觉的隐秘财富中汲取形象,他洞悉客观世界合理外壳下的种种状态,从中捕捉转瞬即逝的偶然和感觉,并将投影于客观现象……”(《诗歌的基础和使命》)伏才的诗也在不知觉中遵循并履行着这种诗歌使命,在感觉和体现的基础上,使主体“生动的经验”得以张扬,使清新自然的表像之外含着人生哲理与意趣。
三、用质朴诠释人性的本真
从文学经验上来看,任何来源于直接和间接的感知都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伏才的诗,最可贵之处,就是能用质朴去诠释人性的本真,而这种写作的本真、表现的本真,从内心深入抒发出来的本真,贯穿他创作的始终,这就使他的诗歌接近了“原生态”般的纯净。伏才能从自己的感知、观望、积累、想像的经验库量,取舍出一段段“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文字,那种平静的铺排和不动声色的述说脱尽华服,特别能走进人的心里,而且给人是“棉质”的感觉,而不是华贵的“丝绸”。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诗歌骨子中的质朴与简约,才使他的诗歌更接近于自然、接近于生活、接近人性。使读者自然走近、用心品尝,这也切合了传统诗的美学原理。
综上所述,诗人的诗歌、真纯、空灵、质朴、清新。他是在用生命体验着生活,并在创作之中获得人性与诗歌的真善美。
但是,伏才的作品也还有欠缺与不足:一是语言不够精当、凝练、缺乏弹性与张力,少了一些诗歌所需的“陌生化”效果;二是意向的选择与创新上还须进一步地尝试与突破,要形成自己诗歌的独特风格;三是构思与风格上不够大气,要注意并跳出“小情小绪”的拘泥与困扰。我们相信:在今后创作路上,伏才一定会为我们创造出更为优美的诗作。
二OO七年七月一日